宋江题反诗--水浒情节的硬伤
宋江题反诗--水浒情节的硬伤

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都知道,第三十九回有‘浔阳楼宋江吟反诗’的情节,是这样写的:
这天,发配江州的宋江,离开牢城到城里寻戴宗、李逵、张顺,没找到,来到江边的浔阳楼上。
“独自一个,一杯两盏,倚阑畅饮,不觉沉醉,猛然蓦上心来,思想道:‘我生在山东,长在郓城,学吏出身,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,虽留得一个虚名,目今三旬之上,名又不成,功又不就,倒被文了双颊,配来在这里。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,如何得相见?’不觉酒涌上来,潸然泪下,临风触目,感恨伤怀。忽然做了一首《西江月》词,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。起身观玩,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,宋江寻思道:‘何不就书于此?倘若他日身荣,再来经过,重睹一番,以记岁月,想今日之苦。’乘着酒兴,磨得墨浓,蘸得笔饱,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道:
自幼曾攻经史,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荒丘,潜伏爪牙忍受。
不幸刺文双颊,那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,血染浔阳江口!
宋江写罢,自看了大喜大笑,一面又饮了数杯酒,不觉欢喜,自狂荡起来,手舞足蹈,又拿起笔来,去那《西江月》后再写下四句诗,道是:
心在山东身在吴,飘蓬江海谩嗟吁。
他时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!
宋江写罢诗,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:‘郓城宋江作……’”
《西江月》中,“攻经史”,“有权谋”,没问题。“虎卧荒丘”、“潜伏忍受”,倒也说出了一个有志者获罪在身的感受。但,“他年若得报冤仇,血染当阳江口”,够凶的,问题就大了。
七绝诗中,心在山东身在吴,飘蓬江海谩嗟吁。人生之慨叹,也算不得反动。关键是后两句:“他时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!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,被封建统治者看作特大反贼。以黄巢作比,比黄巢还狂,自然被看成反诗了。不只黄文炳看着是反诗,我们看着也象反诗。正因如此,才被黄文炳、蔡九之流抓住,打入死牢,候期问斩了。
小说是这样写的,但,细细思量,很有些矛盾。诗词的关键句,不象是宋江写的,联系宋江当时的情况,他似乎写不出、不可能写这样句子。
首先,宋江无写反诗的思想基础。他自幼饱读诗书,受的是儒家教育,听的是太公家教,想的是为国出力,哪里有一点反心?不只连黄巢那样推翻整个政权的心没有,就连晁盖那样劫取钱财的事也不会去做。结合后来的事看,即使宋江在梁山当了“贼首”,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招安,回到朝廷体制中来。如此说来,他哪里有黄巢那种雄视天下的气魄和志向?!劫法场后,他带人杀了黄文炳,确实“血染浔阳江口”了,但那只是个人之间的复仇,与反叛朝廷还是不同的。至于黄巢那种翻天覆地的丈夫作为,终宋江一生,也没有出现。笑黄巢,他是笑不起的。
有人说宋江平时不写,但酒后吐真言,写了潜意识的东西。那也不对。如果他骨子里想反,平时不敢说,或许酒后露峥嵘,可他宋江根本就没有反骨啊!
其次,宋江无造反的行为轨迹。如果想反,早就与晁盖一起上梁山入伙了,还用得着到江州来受这流配之苦?杀了闫婆惜之后,最便利的躲藏地点就是梁山泊。因为他对晁盖等梁山泊头领有恩,曾冒着天大的干系为他们通风报信,使他们摆脱了官府的追捕,到了梁山泊,他宋江会受到很好的礼遇。况且,梁山泊离郓城县又近,去得也方便。可宋江偏不。他舍近求远,去沧州柴大官人处,去白虎山孔明孔亮处,去清风寨花荣处躲藏,就是不去梁山。介绍清风山的弟兄们全伙投奔梁山,他自己却回家看望老父。在发配江州的路上,梁山好汉半路请他上山,他死活不肯。这一切,都是什么原因?因为宋江根据就不想上山落草,认为那是不忠不义的行为,不想在那里毁了自己的清白之身。他满心想的就是老老实实地服刑,等刑满后重新来过,孝亲、报国,做忠臣良将可以走的路。
试想,这样一个怎么都不想反的人,怎么会写出反诗来呢?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
其三,当时没有写反诗的情绪依据。人,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有过激言词。当时,没有使宋江产生过激言词的事件。如果当初官府就要杀他,他刚逃出来,那他有可能写反诗;如果在牢里每天捱打捱骂,屈辱得受不了,他可能写反诗。但,这些都没有啊。发配江州,是自己认了的,盼着回家就行了,还有什么怨词?在江州牢城,并未受苦,每日里还有戴宗、李逵陪着、照顾着,比其他犯人条件优越多了,还有什么怨恨?那个时候,蔡知府没难为他,黄文炳不认识他,没有人加害他,他生的哪门子恨,发的哪门子骚?
虽然唐朝的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写得江州比较沧凉,可白居易有被贬的身世之感啊。江州,这个处于吴头楚尾的州城,其实挺不错的。他宋江在浔阳楼上的感感觉也挺好啊。不信引原文给你看:“少时,一托盘托上楼来,一樽蓝桥风月美酒,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;列几盘肥羊,嫩,酿鹅,精肉,尽使朱红盘碟。宋江看了,心中暗喜,自夸道:‘这般整齐肴馔,齐楚器皿,端的是好个江州!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,却也看了真山真水。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名迹,却无此等景致。’这样的心情,不象是产生过激情绪的时候啊。
通过以上三条可以看出,《水浒传》在此时此地安排宋江写反诗缺乏依据。但故事就这样安排了,安排没商量。一个没有理由的情节,与全书的气脉相矛盾,格格不入。更为严重的是,宋江写反诗,不是一般的情节,而是关系《水浒传》全局发展脉络的重大情节。正象盖十层大楼。下层的圈梁打坏了,影响上层的牢固,甚至会导致整个大楼的滩塌。
你想啊,如果宋江不写反诗,他就不会被黄文炳所害;没有蔡知府欲杀宋江的安排,也就没有了劫法场的活动;没有这一重大变故,宋江也就下不了决心上梁山;宋江上不了梁山,整个梁山的历史就会被改写。
如此分析,就自然得出结论:宋江题反诗这一情节的安排,是《水浒传》一书的硬伤。
好在,读者满足于在对水浒豪侠精神的咀嚼中,沉浸在对该书艺术的欣赏中,对宋江题反诗的合理性也就不细考究,让其虚掩过去了。
宋江写反诗这一硬伤,或许不完全是作者考虑不周。根本的原因,应当与宋江这个人物不想为“匪”却有成“匪”、梁山将领奋起反抗又标榜忠义的矛盾。
谁能编个更加合理且与全书统一的情节,把宋江题反诗的情节替换下来?
-

- 二十年前,公认最好看的十大农村剧,部部都是经典,你看过几部?
-
2025-07-09 21:23:12
-

- 千亿东岭破产之际:东岭集团的陨落和反思
-
2025-07-09 21:20:55
-

- 揭秘72个姓氏背后的故事,这些文化瑰宝你知道多少?
-
2025-07-09 21:18:39
-
- 江西省2022年高考状元出炉,理科状元竟然三人同榜,一起盘点
-
2025-07-07 20:19:50
-
- 国家税务总局任命多名省级税务局局长、副局长
-
2025-07-07 20:17:34
-

- 德国球星尤文图斯中场球员赫迪拉前女友-莱娜.格尔克
-
2025-07-07 20:15:18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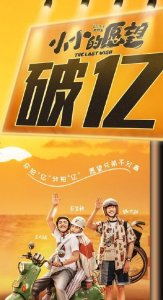
- 真相!小小的愿望票房破亿是什么情况?背后真相详情始末曝光
-
2025-07-07 20:13:03
-

- 36岁张含韵晒三亚游玩照,素颜吊带很清纯,和15岁超女出道时一样
-
2025-07-07 20:10:47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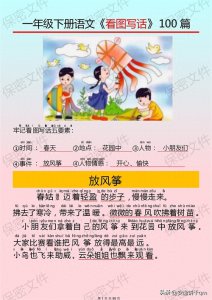
- 一年级看图写话经典范文100篇(含拼音),建议同学们早上阅读
-
2025-07-07 20:08:31
-

- 鹿晗被扔衣服图片曝光,鹿晗为什么被扔衣服背后原因令人震惊
-
2025-07-07 20:06:16
-
- 华裔女性在南非遇害 警方推测系精心策划犯罪
-
2025-07-07 20:04:00
-

- 以媒:伊朗已发布杀害核科学家的4名嫌犯照片,在全国进行搜索
-
2025-07-07 20:01:44
-

- 四川泸定震后大渡河支流湾东河断流:形成堰塞湖 部分居民转移
-
2025-07-07 19:59:29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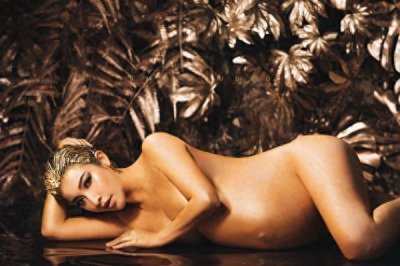
- 许维恩「双手遮半球」辣拍全裸写真 全身上金漆成最「闪」孕妇
-
2025-07-06 08:31:18
-

- 郑爽问吴奇隆二胎计划,吴奇隆笑称: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
-
2025-07-06 08:29:02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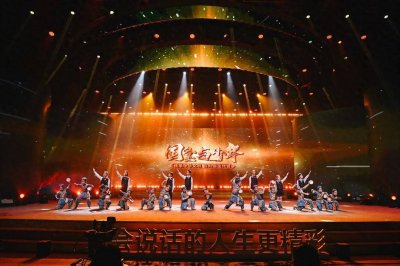
- 四川省第四届青少年“金话筒”颁奖典礼圆满举行
-
2025-07-06 08:26:46
-
- 日媒:福原爱副教授职位不保
-
2025-07-06 08:24:31
-

- 门口6个台阶半天走不上去,女生叹气:“回家也太难了”
-
2025-07-06 08:22:15
-

- 姐夫新电影开拍,权志龙送餐车应援
-
2025-07-06 08:20:00
-

- 新“太空出差三人组”亮相,简历公布!
-
2025-07-06 08:17:4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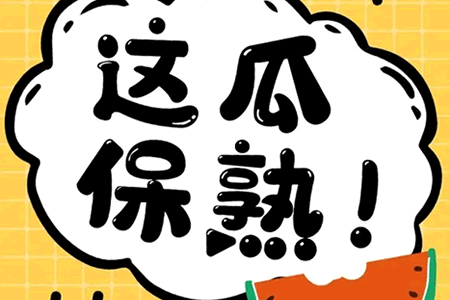 世界综合国力排名(联合国五常综合实力大排名)
世界综合国力排名(联合国五常综合实力大排名) 2023年十大高产玉米品种(排名第一的玉米品种名字)
2023年十大高产玉米品种(排名第一的玉米品种名字)